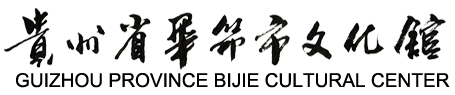摘要:敦煌莫高窟,其“飛天”藝術是絲綢之路上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古代與當時西方文化藝術交流、匯合、融溶、拓展的結果。“飛天”是敦煌藝術的標志,她的內容包含了宗教、世俗生活、歷史事件等,透過形體的夸張、姿態的變化,以音樂的動感來引發人們關于人性的思考和藝術的聯想及審美的情趣,她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輝煌燦爛的華章。
關鍵詞:敦煌莫高窟;飛天藝術;古代音樂;審美意識
一、失落在大漠中的東方明珠
敦煌位于我國河西走廊西端,地處甘、青、新三省(區)交匯處,南有祁連山、北有馬鬃山,東面、西面為戈壁、沙漠。因其綠洲面積僅1400平方公里,且被沙漠包圍,所以是典型的戈壁綠洲區。
敦煌有著源遠流長的古代文明,這一文明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地區的歷史、文化與藝術,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極其光輝燦爛的一章。
敦煌的歷史、文化、藝術曾繼承、發展和延續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與藝術的輝煌,同時又是中西方歷史、文化與藝術相互撞擊、相互吸收的發展,即是我國中原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發展向西推移的結果,又是作為中西交通交流“樞紐”與“咽喉”的中國西部重鎮敦煌與中亞、歐洲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交流交融的結果。敦煌地區促成了中國中原文化藝術與中國西部文化藝術及中亞、歐洲的文化藝術融匯結合后,再反傳進入中原地區并對其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時,中西交匯融合后的文化藝術 也再回旋進入中國西部、中亞和歐洲等地,對其文化與藝術的進步與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敦煌獨特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復雜的歷史進程,充滿著傳奇的色彩。以敦煌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藝術,是敦煌歷史、文化、藝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亦是敦煌作為中國古代及當時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匯合、擴散地的必然結果。敦煌作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至今仍不斷顯示著自己的博大精深,折射著奪目的歷史光輝。眾多古文化遺跡遺址逾越千年漫漫黃沙,靜觀歷史滄桑,至今仍展示著昔日的璀璨與輝煌。
敦煌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其古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地區的遠古時代,有著更適于人類生存發展的良好自然生態環境。自漢代始敦煌就成為中原王朝最為重要的邊疆軍事戰略要地之一,成為中西方陸路交通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梁個紐帶。“絲綢之路”亦不僅僅是絲綢貿易而已,它開通之日就已經在漢代直接轉化為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藝術、生產和生活方式交流傳播的文明之路。遙遙千萬里的“絲綢之路”,通過敦煌這一“咽喉”或“中繼站”、“補給站”,撒滿了包含著東西方各族人們智慧和民族精神精華的種子,撒滿了傳播人類文明的種子。
自此,敦煌成為中國古代歷史發展中最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地,亦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發展之地,同時又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中西方交通交流樞紐,還是中國古代及當時世界藝術最重要的交流、匯合、融合、擴散地,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佛教藝術中心之一。為此,她孕育出了敦煌莫高窟這一不斷顯示其博大精深,至今仍折射著奪目歷史光輝的文化藝術圣地,這一世界文化藝術的寶庫。
莫高窟藝術是敦煌歷史文化的象征;也是敦煌飛天藝術的標志。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公元1900年12月)道士王圓箓發現莫高窟之“藏經洞”,從此,密室開啟,寶藏現于世。這座蘊藏豐富、包羅萬象的古文獻文物寶庫中,滿貯宗教、歷史、文學、藝術和人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文獻文物資料六萬余件。其中有大量佛教、道教、儒學和其他宗教經典著作;還有大量的經、史、子、集、詩、詞、曲賦和音樂、美術、舞蹈、書法、棋弈、通俗文學及水經、地志、歷書、星圖、醫學、數學、紡織、佛像、刺繡、樂譜、畫卷等中華文化的精品珍奇,一應俱全,應有盡有。
敦煌藏經洞遺跡的被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從1905年,俄國奧勃魯契夫強行掠走莫高窟經卷書兩包起,接著英國人斯坦因(1907、1911兩次)、法國人伯希和(1908)、美國人華爾納(1924)、英國人巴慎思(1935、未果)等陸續從敦煌騙、盜或“購”走大量文書、經卷、彩塑、佛像、壁畫等珍貴文物,[雖于1910年敦煌知縣奉命移送經卷于北京,但已步入末途的清政府無法引起重視]。國寶被劫流失,恥也!致使今天有許多珍貴文物史料,還要到大英博物館、美、法、日博物館去查詢了。
1938年,西安藝專李丁隴去敦煌臨摹壁畫,1941年,張大千赴莫高窟臨摹壁畫,(都是在抗戰的艱苦年代),之后舉辦的畫展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從1944年敦煌研究所成立到1994年這五十年間,都是由著名畫家、中國敦煌藝術研究者常書鴻先生任所長。1996年敦煌藝術展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極大轟動。1997年日本將珍藏的8件敦煌文物歸還中國,2000年中國國家文化部舉行系列活動,隆重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之發現,是中國近代乃至世界文化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導致了一門真正世界性的學問——敦煌學的逐漸興起、形成和發展。
所謂敦煌學,就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遺書、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這門學科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大凡中古時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藝術、歷史、地理、語言文字、文學、哲學、科技、經濟、建筑、民族關系、中西交通等各門學科,都可利用敦煌學資料,或填補空白,或糾正前人的錯誤,或改變某些傳統的說法(劉進寶《敦煌學通論》引言)。
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后,在將近半個世紀的長時間內,僅有極少數可稱為先知先覺的中國學者,篳路藍縷,置身于世界敦煌學研究行列中。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海峽峽兩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焚膏繼晷,兀兀窮年,探幽獨微,鍵筆如椽,在文學、語言、歷史、地理、考古、藝術、宗教、天文歷法,以及敦煌學史和敦煌學理論等方面,都有水平相當高的著作,引起了國際敦煌學界的矚目,為中華學術增光添彩,實為學界之盛事,中華之光榮(季羨林《敦煌學研究叢書》序)。
二、敦煌飛天的產生及其藝術形態
敦煌飛天是的敦煌藝術的標志,是敦煌莫高窟藝術的象征。“飛天”是佛經中的乾闥婆(天歌神)與緊那羅(天樂神)的合稱,她們的職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釋,因能歌善舞,周身還發出香氣,所以又叫“香音神”。飛天是敦煌壁畫中一種優美多姿的藝術造型。
敦煌飛天從藝術形象上說,它不但是一種文化的藝術形象,而且是各種文化的復合體。它是不長翅膀,不長羽毛,沒有圓光,借助云彩而不依靠云彩,主要憑借飄曳的衣裙、飛舞的彩帶而凌空的飛天。
在印度佛教中,通常將能在空中飛行的天神稱為“飛天”,“飛天”大都畫在佛窟墓室的壁畫中;而在中國的道教中,則稱為“飛仙”,“飛仙”也大都畫于石窟墓室的壁畫中。
無獨有偶的是,不管是印度佛教中的“飛天”也好,亦或中國道教中的飛仙也好,其相似之處,就是希望“神”和“仙”會飛,都希望墓室主人死后的靈魂能羽化升天。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后,與中國原有的本土宗教——道教相融合。敦煌飛天就是畫在敦煌石窟中的飛天女神,后來就慢慢地成為了敦煌壁畫藝術的一個專用詞和代名詞。原先的樂神干達婆,傳入中國后經中國藝匠們慢慢地演化,最后就變成了后世敦煌石窟中的飛天女神。因此,敦煌的飛天女神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和中國文化長期交流、互相融合和共同孕育而成。
同時,敦煌石窟的飛天女神也是中國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藝術相融合的產物。因此,在飛天的身上有著極期鮮明的中國文化的物?汀K孀歐鸞湯礪邸⑸竺酪帳躋約耙帳醮醋韉姆⒄購托枰商煬橢鸞サ匱莼記迥啃恪⑻逄嵊Ⅳ驃嫫鷂韜桶肯櫨諤煒盞奶烊朔上閃恕?/span>
飛天的故鄉雖在印度,但敦煌飛天卻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這種佛教藝術中能夠在空中自由飛翔的天人,反映了古代人們渴求自由,希望征服太空的美好愿望,敦煌莫高窟藝術中創造了大量多姿多彩的飛天形象。
敦煌壁畫中的飛天,與洞窟創建同時出現,從十六國開始,飛越了十幾個朝代,歷時千余年。在這千余年的歷史長河中,由于朝代的更替,政權的轉移,經濟的發展繁榮,中西文化的繁榮交流等歷史情況的變化,飛天的藝術形象、姿態和意境、風格和情趣、都在不斷地變化。
其演變史可分為4個階段:興起時期、創新時期、鼎盛時期、衰落時期:興起時期(從十六國北涼到北魏,公元366-535年)的飛天粗獷樸拙;創新時期(從西魏到隋代,公元535—618年)的飛天豐富多變;從初唐到晚唐(公元618—970年),貫穿整個唐代,大約300年,鼎盛時期的飛天奔放自由;而衰落時期(從五代至元代,公元907—1368年)的飛天則刻板守舊。
敦煌飛天,雖然是外來藝術,卻是在中國大地上盛開的花朵。為了適應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識、風土人情和審美理想,她必然不斷發生變化。到隋唐時期,達到飛天藝術發展的高峰,創造了具有中國氣派、體現中國審美理想的時代風格和民族風格。
敦煌飛天的創作方法,與敦煌壁畫總的創作方法一樣,經歷了一系列的形象思維過程,即現實——想象——意象——藝術形象。所謂現實,就是百戲和歌舞伎。所謂想象,就是無翼而飛。它體現了中國繪畫美學思想中的“寓形寄意”、“立象以盡意”,甚至“得意忘形”等等重意象、重意境的特色。因此,敦煌飛天是現實生活形象,加上主觀想象(包括聯想、遷想、幻想)并傾注思想感情,熔鑄而成的意象的顯現。她具有中國人的風貌和神采,借助云彩而不依托云彩,僅僅憑借一條舞帶凌空騰飛。這就是隋唐時代審美理想的體現。高度的想象力,賦予了飛天以永恒的藝術生命力。
飛天藝術的主要特征就是飛動之美。敦煌飛天的飛動特色,主要表現在翻飛升騰的俯沖姿勢上,尤其是俯沖的姿態特別優美,它也是敦煌飛天與印度飛天在形象的顯著區別之一。
敦煌飛天的飛動之美,除了體現古代中國和印度美術中的一些特色,尤其是飛動之感,如跳躍、懸騰、浮游、翻飛等姿勢之外,還以飄帶衣裙和云氣飛花為輔助和補充。正是飄帶衣裙和云氣飛花的作用,才解決了體重問題,由于人體的動勢和衣帶、云氣、飛花的相互映襯,才使飛天俊美的面相和體型得到充分表現,從而開闊了敦煌飛天飛動之美的新天地。
飛天就是藝術女神,飛天就是美的化身!天衣飛動,舞帶如風,千年的情結如珠玉般顆顆凝結。敦煌飛天,經歷了千余年的歲月,展示了不同的時代特色和民族風格,許多優美的形象,歡樂的境界,永恒的藝術生命力一直延續至今,令人們虔誠膜拜、崇敬佩服。
三、敦煌飛天中的音樂審美意識
飛天的原型是一種樂伎,也就是所謂的樂神。她們的故鄉原本在印度。她們的任務是在佛國力為佛陀和菩薩布香獻花、從寶及作禮費。她們演奏著樂器,載歌載舞;微笑著棲身于花叢中,輕盈地飛翔于云霄間。
我們知道,在西方也有個家喻戶曉的女神,那就是愛神維納斯。有人說,愛情維納斯美
就美在她那條斷臂上!因為,就是她的那條斷臂的殘缺美,會激發起人們無數美妙的藝術聯想。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東方的女神飛天和西文的女神維納斯,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透過形體的夸張變形和姿態的音樂動感來引發人們關于人性的思考和藝術的聯想及審美的情趣。
敦煌壁畫中的樂伎分為伎樂天和伎樂人兩大類,其中伎樂天又分為天宮樂伎、飛天樂伎、化生樂伎、護法神樂伎、迦陵鳥樂伎、經變畫樂伎等。從整體上看,敦煌飛天特具突出音樂性的“樂伎飛天”,已成為飛天的主流。
中國音樂文化自古就是世界領先地位。以音樂表演為繪畫內容是中國繪畫的傳統,也是一種表達藝術的優勢。佛教只不過是很巧妙地借用了這個題材,并加以發揮,逐漸發展成為佛教畫的重要內容。它利用音樂場面烘托出一種歡樂氣氛,使森嚴的宗教殿堂得到和諧與平衡。在中國,樂器同樣也是一種吉祥物,寓意喜慶歡樂,歷代常將樂器的圖形作為文明的象征,敦煌壁畫中常見的“不鼓自鳴”樂器圖,即是這種文化意識的反映。隨著壁畫的發展,飛天表演音樂的場面愈來愈多,手中所持的樂器也愈見豐富。
敦煌經變畫中,佛殿前沿兩邊排列的樂隊,稱為禮佛樂隊。由于經就畫大小不等,禮佛
樂隊的規模、陣容也各不相同,一般可分為大、中、小三種。大的樂隊為每邊18人以上,小的多為一邊2至4人。
有的大型經變畫,多達三層樂隊。兩側樂隊席地而坐,中間有舞伎表演,有的空手而舞,有的則反彈琵琶或持腰鼓。從敦煌壁畫樂、舞伎的排列形式和樂器使用范圍來看,它基本上是隋唐燕樂的編制,經變畫就是以此為模式進行繪制的。
在壁畫中,凡描繪人間世俗的活動,其中奏樂作舞者,都是伎樂人。伎樂人也稱“供養樂伎”。它是社會現實生活的直接反映,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世俗樂舞,現實性較強。
唐代國力強大、經濟繁榮、豐富繁榮的文化藝術、開放的國策,再加上不斷吸收、創新、發展,使敦煌的飛天達到了繁榮鼎盛的時期。唐代的飛天多畫在大型經變畫中。一方面為大型經變畫中的佛陀說法場面,散花、奏樂、歌舞作供養;另一方面表現大型經變畫中佛國天堂——極樂世界的自由歡樂。有的腳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揮臂,騰空而上;有的手捧鮮花,直沖云霄;有的手托花盤,橫空飄游;飄曳的衣裙、飛卷的舞帶,給人一種豪邁有力、奇姿異態、變化無窮的飛動之美。
唐代飛天伎樂手中所持的各種樂器,對研究世界樂器史是極其珍貴的資料。隋唐時代是敦煌飛天完善的高峰,她們動感靈活、姿態豐富,所持樂器及演奏狀態,充分反映了當時的音樂水平。觀查此時樂伎飛天持奏的樂器主要有橫笛、篳篥、排簫、笙、胡角、琵琶、五弦、阮、箜篌、腰鼓、方響、鑼等,許多樂器延傳至令仍在使用。唐代樂伎飛天使用樂器種類繁多,持奏形態、優雅,人體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有力,是敦煌飛天的精美之作。
現僅以四簾樂伎飛天為例以識其音樂意識。
 一、反彈琵琶:
一、反彈琵琶:
琵琶在敦煌飛天樂伎中占有突出位置,圖形最多,被廣泛運用。由于在大型歌舞《絲路花雨》中對她有了藝術的詮釋,使反彈琵琶形象成了敦煌飛天的代表(現在已是敦煌市的標志)。琵琶是中國古代重要彈撥樂器。東漢劉熙《釋名·釋樂器》曰:“批把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漢代定型為四弦十二品位。唐代它的演奏技法逐漸豐富和發展,既用于歌唱、曲藝、戲曲和歌舞的伴奏,也用于獨奏和樂器合奏。琵琶在古代詩詞中反映甚多,據考證,飛天反彈琵琶的“彈”,是散開五指輕輕拍擊,由此可知,這種反彈琵琶的舞蹈,動作輕盈,節奏平靜徐緩。不知確否,尚待學者們繼續研討論證。
二、橫笛: 飛天樂伎持奏的橫笛是今笛的原型,古多“篴”。朱載堉《律呂精義》曰:“篴與笛意義并同,古文作篴”。橫笛吹管樂器中之主要者,所以在飛天壁畫中數量很多,僅莫窟統計,就繪有500余幅,敦煌所繪橫笛,始見于北京,歷代延續不斷,直至宋元。從其形制音孔及演奏方法看,都與今日之橫笛基本一致。壁畫中橫笛的主要特征是不用笛膜。橫笛飛天樂伎動作輕盈、神態逼真、姿勢優美,讓人們感受到似乎笛聲已從天上飄逸下來…… 她是莫高窟壁畫中之佼佼者。
飛天樂伎持奏的橫笛是今笛的原型,古多“篴”。朱載堉《律呂精義》曰:“篴與笛意義并同,古文作篴”。橫笛吹管樂器中之主要者,所以在飛天壁畫中數量很多,僅莫窟統計,就繪有500余幅,敦煌所繪橫笛,始見于北京,歷代延續不斷,直至宋元。從其形制音孔及演奏方法看,都與今日之橫笛基本一致。壁畫中橫笛的主要特征是不用笛膜。橫笛飛天樂伎動作輕盈、神態逼真、姿勢優美,讓人們感受到似乎笛聲已從天上飄逸下來…… 她是莫高窟壁畫中之佼佼者。
三、排簫
中國古代編管樂器《世本》“(排)簫,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排)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漢唐以來石刻、壁畫及隨葬陶俑中常可見吹奏排簫的形象,宋代以后民間失傳,只用宮廷雅樂。湖北曾候乙墓出土的排簫,

竹制十三管,是目前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實物。敦煌飛天樂伎中的排簫,位置顯著,造型華麗,極富仙樂幻覺的意境。莫高窟繪有排簫300余只,壁畫中的排簫始自北魏,直到元代,大部分伎樂里都有,可見其在當時樂隊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腰鼓:
中國古代擊樂器,源自北方民間。但本文所述敦煌飛天樂伎所持的腰鼓,不是今天(用雙手各持一木棍擊奏)的型制。
 敦煌腰鼓的特征為細腰,形狀如兩個碗,底部對接而成,兩端張以皮革,以繩收束,使皮膜繃緊,敲擊發音。演奏方式是系于腰間,或置于面前,用手拍或杖擊發音。敦煌壁畫中的腰鼓,從北涼到元代,一貫始終,從未間斷,而且形類繁多,幾乎每一只,都有其特色。它不僅出現于樂隊中,而且是舞伎表演的重要道具,是一種具有高度工藝水平的裝璜性樂器。
敦煌腰鼓的特征為細腰,形狀如兩個碗,底部對接而成,兩端張以皮革,以繩收束,使皮膜繃緊,敲擊發音。演奏方式是系于腰間,或置于面前,用手拍或杖擊發音。敦煌壁畫中的腰鼓,從北涼到元代,一貫始終,從未間斷,而且形類繁多,幾乎每一只,都有其特色。它不僅出現于樂隊中,而且是舞伎表演的重要道具,是一種具有高度工藝水平的裝璜性樂器。
敦煌樂伎飛天的優美形象及她們展現的藝術姿態,是由于古代各民族的音樂意識所決定的,但可惜的是,這些飛天的音樂內容,它們在千年歷史長河中早已凝固在莫高窟冷凌的壁畫中,今天已無法現現。所幸的是,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一批遣書中的曲譜,今人稱為“敦煌曲譜”,這是極為珍貴的音樂史料。
“敦煌曲譜”的抄寫年代是公元934年閏正月,從而可知,這些樂曲的存在年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由于這些樂曲早已失傳,記錄樂曲的記譜法已被遺忘,所以解釋敦煌便成了一大難題。
多年來,已有一批中外學者對敦煌曲譜進行考證、研究、解釋、譯配工作,例如:林謙三、平出久雄(日本)、任二北、趙如蘭(趙元任之女)、何昌林、葉棟、席臻貫等,他們對破譯敦煌曲譜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其中,我個人對葉棟先生的研究成果尤為欽佩,并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二十年前,筆者就注意到國內輿論界對葉先生對敦煌曲譜。
一、婆羅門 敦煌曲子《仁智要錄》譜

二、慢曲子·西江月 《敦煌唐人琵琶曲譜》第13曲

從敦煌樂伎飛天折射出我國的唐代音樂——尤其是宮廷音樂——是我國古代音樂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西域絲綢之路的的開辟溝通了我國與中亞并遠至歐洲的商貿關系,隨著中西文化的布不斷交流與融合,使宮廷燕樂和禮儀性、娛樂性的歌舞音樂得到很大開拓,并逐漸形成了具有新的民族風格特色的隋唐音樂。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音樂藝術的黃金時代,也是飛天發展的最高峰。飛天的形成是多種因素交織、積淀的結果。她是以歌舞伎為藍本,并大膽吸收外來藝術營養,促進傳統藝術的改變,從而創造出具有表達中國音樂意識、風土人情和審美思想的飛天形象。
參考文獻:甘肅教書出版社
1、劉進寶著《敦煌學通論》序,P138、P141.
2、鄭汝中著《敦煌壁畫樂舞研究》,P29(圖一)、P62